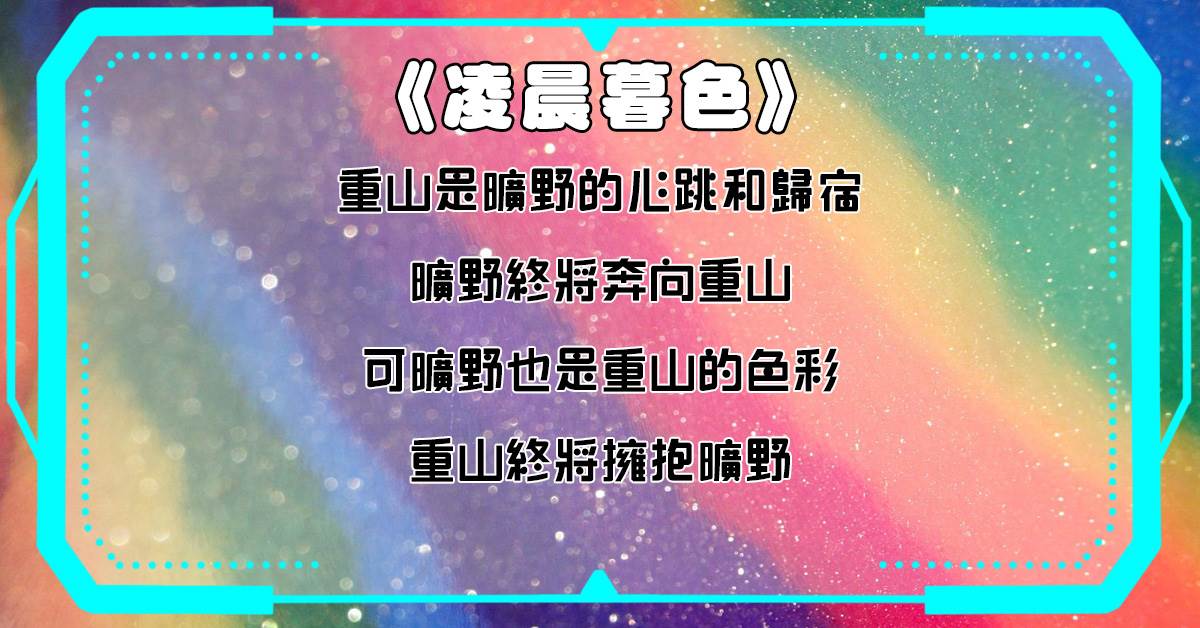《凌晨暮色》第28章
靳重山先一步走入院中,回過頭來看斯野。
背對光線,陰影將靳重山的鼻梁修飾得更加挺拔,眼睛更加深邃。
灰藍變成不見底的黑,像澄澈的潭水,倒映著斯野的模樣。
沒有驚訝,沒有不悅,只是眉心很淺地皺了皺。
斯野手心出汗,雙腳像踩在燒紅的炭上。
他不得不快步向前走,直至也走到院中的橘黃色光芒下,走到靳重山面前。
他身高足有一米八,從未想過有朝一日,當自己情不自禁想要親吻一個人的時候,需要踮起腳尖。
他像是被數條看不見的細線牽引著,汗濕的手虛托住靳重山的后頸,仰起臉,生澀地碰觸靳重山的唇。
他不敢睜開眼,不知道冒犯到這種程度,靳重山正用怎樣的視線打量他。
那就索性不看。
他喝了一杯烏蘇,但比烏蘇更醉人的是靳重山的氣息。
他豁出去了,此時他只想當人們眼中最俗的那一種——在旅途中倉促又隨便地愛上一個人。
他沒有談過戀愛,更沒有親過人,自以為吻得十分霸道,堪比偶像劇里將美人堵在墻邊的惡霸。
但事實上,他只是毫無章法地貼著靳重山的唇,啄一下,又蹭一下。
忽然,鋪灑在臉上的氣息變得粗重,后腦被一只干燥的手扣住,掙脫不得。
他驀地睜開眼,驚訝與茫然在他瞳底凝作一團輕晃的光。
靳重山垂著眼瞼,眼里的平靜與平常略有不同,好似深潭之上刮起風,吹散落在潭水中的星子。
斯野腦海空白了片刻,遲鈍地反應過來,靳重山在回應他這個虛張聲勢的惡霸。
ADVERTISEMENT
夜很深,吻卻很淺。
燈光將這一切變得不真實,但熱烈的心跳又告訴斯野:不,這是真實的。
靳重山松開他,視線落在他臉上,看得十分專注。
他臉頰發燙,不知道靳重山此時正想著什麼。
他們認識不久,但他已經明白靳重山是少說多做的性子,能用行動解決的,就懶得陳述。
所以剛才的吻,是接受了他的示愛?
還記得初上帕米爾高原的那天,他問靳重山,為什麼艾依不行。
除了民族不同,靳重山還說,因為不喜歡。
不喜歡,所以直白了當。
喜歡,哪怕尚且只有一點,所以縱容他的冒犯。
斯野胸膛灼熱柔軟,不禁道:“哥……”
靳重山好似終于觀察夠了,側過身,“夜里溫度低,進屋。”
塔爾鄉的房子是新蓋的,但住在牧民家還是只能睡石炕,被子褥子都是自己鋪。
斯野不干點什麼,手腳好像都找不到地兒放,搶在靳重山之前把褥子抱下來。
石炕很長,并排睡五個人都沒問題。
他剛強吻了人家,這會兒后知后覺害起臊,將兩床褥子各擺一頭,還發神經地在中間堆起兩床被子。
靳重山看了會兒,把那兩床被子抱走了。
斯野老實地跪坐在自己的褥子上,“嗯?”
只見靳重山又把褥子往他這邊拉,像昨天那樣拼在一起。
“靳,靳哥?”
“我喝過加奶油的奶茶了。”
斯野臉頰頓時紅得如同燒過頭的爐子,“我,啊,那個……我們……”
靳重山又靠近,親了親他亂七八糟吐著詞語的嘴。
他馬上安靜下來。
三分鐘后,他匆匆跳下石炕,“我去洗把臉!”
燒熱的水澆在臉上,斯野捂住額頭,拼命讓自己不那麼躁動。
ADVERTISEMENT
他現在沒辦法思考太多東西,吻了人家,說了一堆話,可然后呢?該做什麼?
他根本沒有想好。
他就是被小楊點了火,又讓烏蘇助了興,才倉皇將心捧出來。
做好了被拒絕的準備,唯獨沒有做好被接受的準備。
現在他就像即將參加期末考的學渣,別說老師劃的重點一條不知道,就連筆和準考證都不知丟在哪個角落。
斯野回到屋里時,靳重山拿上洗漱用具去衛生間,大燈已經關掉,只剩一盞夜燈。
斯野鉆進被子,聽水聲和自己的心跳。
靳重山出來,推開房門,大約是去院子里晾毛巾,不久又回來。
那盞夜燈也熄滅,斯野感到身邊的被褥動了動。
等到動靜停歇,他低聲說:“哥。”
“嗯?”
“我沒有理解錯嗎?剛才你吻我,是那個意思?”
一段無法度量的沉默后,靳重山說:“嗯。”
斯野在被子里緊緊抓住自己的衣服,“我可不可以知道,是什麼時候?”
“……不知道?”
這個答案出乎斯野的意料。
不能、不會、不知道,這樣的詞語仿佛永遠和靳重山無關。
他是帕米爾高原的雄鷹,是喀喇昆侖的山神。
雄鷹和山神,竟然也有不知道的事?
斯野往靳重山那邊挪了挪,黑暗讓他更加大膽。
在他就要碰到靳重山時,靳重山說:“你呢?”
“我?”他想了想,裝作油腔滑調,“我應該是一見鐘情。”
這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真假。
靳重山摘下墨鏡時,他確實被那雙灰藍色的眼睛所吸引。
可那算不算鐘情?
如果沒有后面發生的事,大約不算。
但人的情感就是那麼復雜,環環相扣,一見鐘情看似膚淺,但缺少任何一環,都不過停留在驚鴻一瞥。
靳重山很輕地笑了笑,“你們創造的成語很美。

 上一章
上一章
 下一章
下一章
 目录
目录
 分享
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