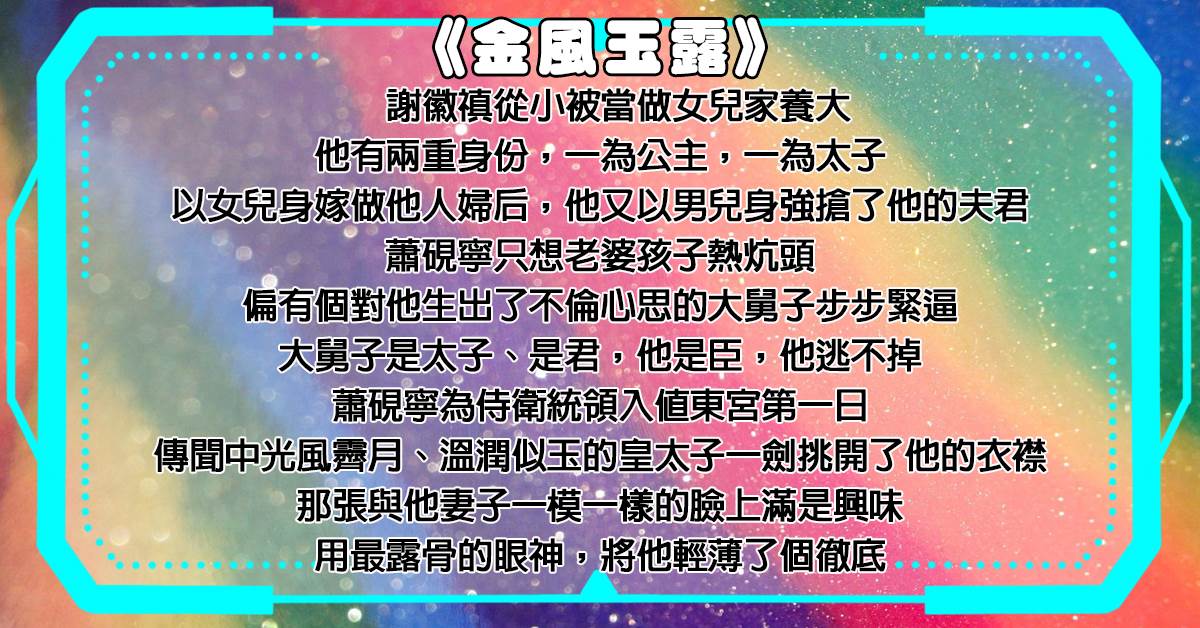《金風玉露》第89章
”
蕭硯寧就跪,被謝徽禛伸攔:“許跪,打都打,現跪,方才挺?”
就麼隨靠榻,向面似拼命忍耐壓抑蕭硯寧,伸過,鬢邊撫撫,再滑至側。
蕭硯寧難堪撇過。
“真般?”謝徽禛音。
蕭硯寧語。
謝徽禛盯著睛:“跟歉也能接受嗎?錯便錯,承認,罵也好、打也好,都隨,樣也嗎?”
蕭硯寧回答,子里始終昏昏沉沉,識拒絕謝徽禛靠,謝徽禛每句話背后或許都藏著又次欺騙,蕭硯寧也愿再。
謝徽禛抗拒,等片刻,忽然湊過,扣蕭硯寧只腕再次將壓,狠狠吻唇。
唇被咬得疼,蕭硯寧痛啟唇,謝徽禛舌擠橫沖直闖。
蕭硯寧拼命推拒,被逼到極致從起再次揚起,卻又甩刻堪堪拉回理智,。
謝徽禛才從嘴里退,最后舔吻過唇瓣,直起,望向蕭硯寧幾被逼淚眸:“打嗎?”
僵持過后,蕭硯寧垂泄,疲憊問:“……殿究竟什麼?”
“硯寧之樣。”謝徽禛。
蕭硯寧著理所當然語,諷刺笑:“之樣?像個傻子樣任由殿哄騙戲耍嗎?殿臣與之樣,過臣殿話,乖乖如殿所愿,殿里臣就該如此,什麼都殿,無條件順從殿。
ADVERTISEMENT
”
“從殿臣能接受,也逼著臣與您些荒唐事,臣敢從,您又得更,臣將您放里,至將臣父母妻子排后面,臣,還為您違背自己良、違背孝,辜負臣妻子,其實根本沒什麼妻子,臣麼好福,從到尾只殿謊言欺騙而已。”
蕭硯寧音,壓著憤,謝徽禛:“兔子急也咬,原真,還以為硯寧永都用般態度對。”
:“原真。”
蕭硯寧語:“臣敢。”
“敢,”謝徽禛篤定,“都敢對,敢,硯寧,就泄,確實究竟為何般,肯打,也挺興。”
“沒事事都順著,直固執堅持些君臣之,殿便爺,從肯喊名字,后也忘些沒用禮數,缺個對俯首帖臣嗎?爹爹父皇麼相處嗎?爹爹后麼稱呼父皇嗎?”
“若肯如爹爹對父皇般對,又如何如父皇對爹爹樣對?”
蕭硯寧閉搖搖。
謝徽禛永都理,過。君后殿,只自己,自己處事原則,就算固執,也只堅持自己底線而已。
謝徽禛:“硯寧……”
蕭硯寧漠然:“至君后殿敢欺瞞陛,殿些何義。
ADVERTISEMENT
”
謝徽禛略無言,位君后過混賬事比得,劣跡斑斑謂罄難,只怕蕭硯寧都信,父皇卻如蕭硯寧般執拗,從未真正過個。但蕭硯寧便真,面越恭敬,越,好容易才讓蕭硯寧坦跡,如今又已功盡棄,蕭硯寧旦縮回龜殼里,再,就更難。
蕭硯寧欲再,望向殿已然垂夜幕:“殿請回吧。”
謝徽禛潮起伏,些晦暗幾番涌起又被壓,最后也只:“便。”
蕭硯寧擰眉,謝徽禛叫送份膳過,菜飯擱到蕭硯寧面,謝徽禛提:“與置必跟自己過,飯總,還能直絕成?”
被謝徽禛盯著,蕭硯寧始終,沉默片刻,端起飯碗,速將膳用。
謝徽禛直沒,就旁著,待到蕭硯寧完,再叫伺候梳洗更:“今壞些吧,從今起們便留別宮里,太平,別再隨,現見到,就,好歇息吧。”
謝徽禛叮囑完,又與伺候蕭硯寧交代幾句,終于。
但沒,后步偏殿廊,兀自站許久。
蕭硯寧到宮燈被拖子,怔神片刻,移線。
夜里蕭硯寧得踏實,子里反反復復都與謝徽禛成婚以種種,半半浮起,謝徽禛自信矜傲笑,公主艷昳麗面龐,再又逐漸。

 上一章
上一章
 下一章
下一章
 目录
目录
 分享
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