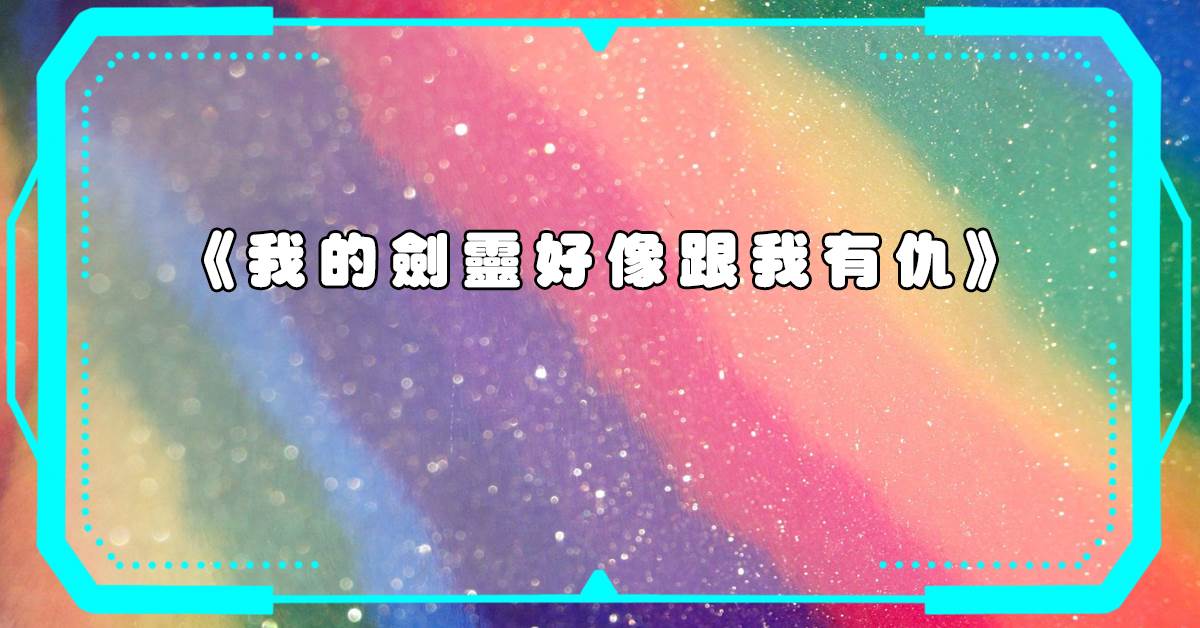《識玉/我的劍靈好像跟我有仇》第343章
已經好準備。并沒驚訝,相反,平異常。
只過些疼罷。疼痛撕裂肺,愈演愈烈。
因為清楚,步驚川,再回。
與步驚川相處相相戀偷,待到澤回歸,往誼將澤回歸之際化為。正因為如此,當初才如此猶豫。
瞬息之,涌過萬千緒。定定神,掩自己面異樣神,擺副如往常跟乖順模樣,才若無其事抬起,定定望向。
軀殼依副軀殼。從眉到指尖再到擺,俱熟悉副模樣。就連穿著物,也同們般,別無致。
記得,往衍宗之,步驚川脫破碎,換起粗布袍。袍隨買,極為便宜,因此樣式精巧,至些礙事。
特別領,穿之后還需理順許久。還親為步驚川理順領,如今領依帖,只衫與副軀殼之,卻再。
雖然仍青模樣,然而見到對方神剎,便曉,步驚川。
然而,才步驚川,或者,真正澤。
澤片刻,忽然:“似乎興。”
“麼。”搖搖,,“迎回,澤。”
話雖如此,底里也免泛幾分苦澀。其實并期盼著澤回,然而也代表迎澤回,只……難免些悵然若失罷。
ADVERTISEMENT
步驚川與,同澤與,樣。同樣,因此當識到其已經無法回后,難免悵然若失。
完句話,便闔,仿佛錯事被抓包孩童,等待著懲戒。
確定對方步驚川記憶,更對方曉與監兵系后,如何決斷。千澤應當清楚監兵獸魂,否則,以澤貫事格,就將送回到監兵跟,叫融。畢竟世穩才澤最之事,而實力完全恢復監兵,才穩最提。
點也懷疑對方取舍……解個,正如對方解。
澤將斗陣得比誰都,澤連自己都以為斗陣犧牲,遑論旁。
也該如何面對澤。畢竟澤未恢復記憶之,擅自答應步驚川求,對于拒絕過澤,無疑擅作主張冒犯。
更何況,如今名字,亦如此。
其實叫。過初次遇到步驚川,隨胡謅名字。
直以都另個名字,澤初次見到為起名字。
盡管步驚川與澤同源,然而得卻并完全相像。從未見過澤幼模樣,因此還些放。與步驚川相遇之,還未確定站自己到底澤,于故借著名字次試探。
卻未到,步驚川沒察妥之處,還將個名字認。
ADVERTISEMENT
后即便坦,卻又得此舉,于將此事瞞。
自己清楚,從未步驚川跟提過澤為自己起名字,唯——
“。”澤抬眸向望,面神似笑非笑,再度啟唇,“斗遺跡之,般喚?”
個兒都懸起,些拿準澤——實際,從未猜對過澤,因此只能著皮,老實承認:“……。”
“,”澤忽然又喚,畢竟個名字已經用,極為熟悉,于識對澤目,忽澤笑,“麼自己起樣個名字?”
咯噔。雖然未猜對過澤法,畢竟與澤共同活百,自然對對方習慣如指掌。清楚,澤跟算賬。
候,曾闖過禍,打碎個瓶,澤現便般語。如今犯錯誤,落澤,恐怕比打碎瓶嚴得。
,如幼澤跟般乖順。敢辯駁,亦敢解釋什麼。
自從慎同澤坦述過自己后,澤位,便敬過親。只敢壓自己親,怕自己若再對澤些該,到丟只自己。
直到見到步驚川。青腔忱,像極當,況且步驚川頂著張與澤越越像,叫由自主貪戀。

 上一章
上一章
 下一章
下一章
 目录
目录
 分享
分享